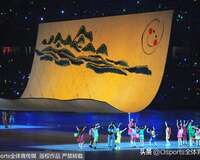一个北京知青的夏县记忆(17)
2024-01-19 来源:你乐谷
1969年春天,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妈妈来信,我心里非常不安。母亲在文革中是被批斗的。说她是特务,是国民党军官的妹妹,是右派分子的老婆,等等。光是为了查清她的特务身份,外调人员自称已经在全国跑了几万公里了。母亲的生活十分艰难,仅凭自己一个月五十元的工资要养活我们四个孩子,后来大妹妹和我一起去了山西,小妹去了内蒙兵团,家被彻底拆散了。要是妈妈……我和大妹不敢多想,商定由我无论如何要回去看看。我没钱买车票,只能扒火车回去。一路上有惊无险。到家一看,母亲果然被关起来了,只剩13岁的小弟弟一人在家。我到单位去找,见到了被关押劳改的妈妈。好在是没几天妈妈就被允许回家了,情况多少有了些缓解。而我也必须回村销假了。母亲无端受到如此羞辱,我作为儿子却无能为力。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回山西还是扒火车,仅仅补了一张3.80元的车票(从北京补到定县)。我的“成功”经历鼓舞了同学,也都开始盘算扒车回家。夏天干完麦收,我们约了几个人,有我和我妹妹,有树臣、建民,有一鸣,好像还有一两个,开始了回北京的冒险之旅。但当时正赶上临汾武斗,南同蒲铁路不通了,只能走河南。
山西两派武斗,战场在临汾。我们村里都派了人前去参战,不参战的也要捐粮捐钱,七队有个打过内战的老兵,他去参战了。队里社员好像也都捐了些钱粮,但为谁打仗、为什么打仗都不知道。武斗造成南同蒲线不通车,如果要回北京就要绕道河南走陇海线。从庙前坐汽车到平陆茅津渡,坐船过黄河到河南三门峡,从三门峡到郑州,从郑州再到北京。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线。由于没有钱,我们是要全程扒火车的,一路上惊险不断。
我们一大早就从村里出发了,临行时老乡送了我们好几十个煮鸡蛋,差不多整整一军挎,一鸣背着。到了庙前坐开往茅津渡的汽车。车是一辆解放卡车,没有座,人全站着。车厢里人很多,人挨人挤得动弹不得。路上肚子饿了想吃鸡蛋,但是被挤在车向中间的人根本找不到地方把鸡蛋磕开。一鸣有个办法,他腰上系着那种帆布皮带,他把鸡蛋在皮带扣上磕,我挨着他,我的鸡蛋是他帮我磕的。
在茅津渡等船时碰到一群北京知青,有男有女。有个男孩低声对我说,注意点身上的钱,我们的钱都集中放女同学身上。我说,我们也是。其实我们哪儿有钱!
黄河渡船是木帆船,船舱很深,岸上的人要跳下去,人在船舱里站着。黄河水没什么浪,但水流较急。河水是棕红色,很浑。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在河里游泳,一个人还与我们的船碰了一下,很悬。
茅津渡对面就是三门峡市。我们上了岸,在车站附近饭馆吃了点儿饭,就往车站停车场走去。路上又远远看见那些同船过来的北京知青,他们有钱,是去售票处买票的。我们有些难为情,就躲着他们,当然更要躲着铁路人员,绕着从车站最西头的大铁门溜进了站台。又从站台跨过铁轨,到了货运火车停靠的地方,选了一个较为干净的空车厢,车厢离地面很高,大家互相帮着爬了上去,半拉上车门,静静地藏在车厢里。车什么时候开?是不是往郑州方向开?不知道。
天渐渐晚了,车咣咣地动了好几下,忽然半关着的门被打开了,跳上三个人来,我们吓得够呛。那三人倒是很客气地跟我们打了打招呼,原来他们也是扒火车的。攀谈中得知他们不是知青,就是在铁路上来回跑,“吃火车”的。他们说这趟车快开了,就是去郑州方向。他们不去郑州,好像是去一个什么小站,说是要去“吃”一辆往回走的客车。他们也不避讳,说“吃”火车就是夜里把旅客的旅行包扔下来,底下有人捡。
车终于开了,天也完全黑了。车里车外一点亮都没有。那三个人唱起歌,全是外国名歌,唱的还好听。我们这边,建民带头唱起了《喀秋莎》《红梅花开》等苏联歌曲。我素来不喜欢苏联歌曲,没跟着唱。后来到了一个小站,那三个人下车了走了。记得他们说过,陇海线有几处他们存钱存东西的站点。还说你们坐船过黄河时看到游泳的人就是他们。真不知道,社会中还有这样的人、这样的生存方式。
回山西还是扒火车,仅仅补了一张3.80元的车票(从北京补到定县)。我的“成功”经历鼓舞了同学,也都开始盘算扒车回家。夏天干完麦收,我们约了几个人,有我和我妹妹,有树臣、建民,有一鸣,好像还有一两个,开始了回北京的冒险之旅。但当时正赶上临汾武斗,南同蒲铁路不通了,只能走河南。
山西两派武斗,战场在临汾。我们村里都派了人前去参战,不参战的也要捐粮捐钱,七队有个打过内战的老兵,他去参战了。队里社员好像也都捐了些钱粮,但为谁打仗、为什么打仗都不知道。武斗造成南同蒲线不通车,如果要回北京就要绕道河南走陇海线。从庙前坐汽车到平陆茅津渡,坐船过黄河到河南三门峡,从三门峡到郑州,从郑州再到北京。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线。由于没有钱,我们是要全程扒火车的,一路上惊险不断。
我们一大早就从村里出发了,临行时老乡送了我们好几十个煮鸡蛋,差不多整整一军挎,一鸣背着。到了庙前坐开往茅津渡的汽车。车是一辆解放卡车,没有座,人全站着。车厢里人很多,人挨人挤得动弹不得。路上肚子饿了想吃鸡蛋,但是被挤在车向中间的人根本找不到地方把鸡蛋磕开。一鸣有个办法,他腰上系着那种帆布皮带,他把鸡蛋在皮带扣上磕,我挨着他,我的鸡蛋是他帮我磕的。
在茅津渡等船时碰到一群北京知青,有男有女。有个男孩低声对我说,注意点身上的钱,我们的钱都集中放女同学身上。我说,我们也是。其实我们哪儿有钱!
黄河渡船是木帆船,船舱很深,岸上的人要跳下去,人在船舱里站着。黄河水没什么浪,但水流较急。河水是棕红色,很浑。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在河里游泳,一个人还与我们的船碰了一下,很悬。
茅津渡对面就是三门峡市。我们上了岸,在车站附近饭馆吃了点儿饭,就往车站停车场走去。路上又远远看见那些同船过来的北京知青,他们有钱,是去售票处买票的。我们有些难为情,就躲着他们,当然更要躲着铁路人员,绕着从车站最西头的大铁门溜进了站台。又从站台跨过铁轨,到了货运火车停靠的地方,选了一个较为干净的空车厢,车厢离地面很高,大家互相帮着爬了上去,半拉上车门,静静地藏在车厢里。车什么时候开?是不是往郑州方向开?不知道。
天渐渐晚了,车咣咣地动了好几下,忽然半关着的门被打开了,跳上三个人来,我们吓得够呛。那三人倒是很客气地跟我们打了打招呼,原来他们也是扒火车的。攀谈中得知他们不是知青,就是在铁路上来回跑,“吃火车”的。他们说这趟车快开了,就是去郑州方向。他们不去郑州,好像是去一个什么小站,说是要去“吃”一辆往回走的客车。他们也不避讳,说“吃”火车就是夜里把旅客的旅行包扔下来,底下有人捡。
车终于开了,天也完全黑了。车里车外一点亮都没有。那三个人唱起歌,全是外国名歌,唱的还好听。我们这边,建民带头唱起了《喀秋莎》《红梅花开》等苏联歌曲。我素来不喜欢苏联歌曲,没跟着唱。后来到了一个小站,那三个人下车了走了。记得他们说过,陇海线有几处他们存钱存东西的站点。还说你们坐船过黄河时看到游泳的人就是他们。真不知道,社会中还有这样的人、这样的生存方式。
 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
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