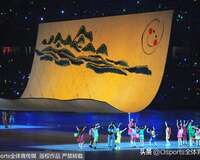一个北京知青的夏县记忆(18)
2024-01-19 来源:你乐谷
火车继续开。不知开到何处是一站。后来到了渑池的一个货车站,看意思会停一段时间。我们大家渴的不行,就都下了车,沿着铁轨往前走,借着货车站的灯光,找到了一个自来水管,大家轮流喝了个痛快。刚喝完,忽然听到火车咣当一声,应该是车头挂钩,估计车要开了,我们连忙往回跑。这时车已经缓缓移动了,由于没有站台,车厢是要爬上去的。大家急忙往上爬。我没爬,一直帮着把人一个一个从下面往上抬,一边抬一边还要跟着逐渐加快的火车跑。刚才在往回跑的时候,我见到我们车厢前两节有一节油罐车,油罐后边有一个带扶手的小铁梯。由于车越来越快,我怕我往车厢上扒会滑到车轮下,那太危险了。于是我加速往前跑,跑到油罐车的铁扶梯那里,抓住扶手,顺着梯子上了油罐车。
油罐车上没有什么地方可呆,我只能坐在铁条焊起来的栅板上,用手抓着扶手栏杆。车子开快了,有些晃,我双手使劲抓牢,生怕被甩下去。当时天黑极了,周围远近都一点儿光亮没有,而只有我身子下面铁条缝隙间,可以看见车轮与铁轨摩擦出的一串串火花。我索性闭上眼睛,心里唯一盼着的就是快点儿停车。没想到的是,火车忽的一下进了一条隧道。隧道里,火车的轰鸣一下子变得无比巨大,好像整个世界都变成声压要把我碾碎。太可怕了,这就是通往地狱的通道。我身子蜷缩着,恐惧地承接着这一切。火车在隧道里足足开了有半个小时,这是我平生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,肯定是我所能承受的极限!
万幸那列火车应该是不是烧煤的,否则煤烟也肯定会把我呛死。火车出了隧道又开了一段时间,我感觉到车减速了,还不断地变岔道,知道要停车了,熬过来了。
由于上车的时候太乱,以致大家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。大家都急的够呛,当我再次见到大家的时候,都乐坏了。特别是我的妹妹。
火车进了编组站,广播里不断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编组口令。谁知道我们这车还走不走啊?我下车找了一位扳道工,扳道工看出我们是知青,就说这车不走了,旁边这车走,上旁边车吧。
扒火车
我们全都下了车,到旁边车上一看,原来是一辆运煤车。上吧,没办法。几个人就在高高的煤堆上坐了下来,车很快就开了,等速度开起来,车倒是不晃,但一阵一阵颠得厉害。我们都坐在高处,连个能扶的地方也没有,只能互相紧拉着手。而我腾出一只手,死劲扒住一个大煤块。当时还是黑夜,七八个人坐在煤车顶上,随时都有被颠下来的危险。这个场景,常人绝难想象。
天蒙蒙亮,车停了。忽然看见从后面煤车上爬起来几个人,满身满脸都是黑的,其中一人还戴着眼镜,形象就像刑场上的政治犯。原来他们也是扒车回北京的知青。看到他们,我们都笑了。再看看自己,其实一毬样。我们都是“政治犯”。
大家一起下了车。那是一个很小的客车站,有个非常小的候车室,候车室门前有个卖早点的摊儿。大家在自来水管那儿洗了洗脸,吃了油饼大米粥,就又进到站里,准备再找辆车往郑州走。建民找到我,说站里有一群人一直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,说咱们得提防着点。我原来没注意,经建民一提醒,我也觉得确实有问题。我说咱们赶快找个车厢躲进去。我们找了个空车厢,为了防身,我们特意从铁轨旁搬上来一堆石块儿。
车开了,车站上那些人从开着的车门看见了我们,他们开始用石块砍我们,我们也开始用石块还击,我们一边还击一边哈哈笑,心想车开了,你们想追也追不上啦。
车开出一、二百米忽然停了,紧接着又往回倒,竟又倒回车站里,只不过是换了旁边的另一条轨道,原来车是在换轨。这把我们可吓坏了,只能关上车门躲着。幸好车又开了,直到真的开起来大家才放下心。一分析,估计我们第一次走的时候,那帮人也没想到车还会回来,就散了。躲过一劫。
油罐车上没有什么地方可呆,我只能坐在铁条焊起来的栅板上,用手抓着扶手栏杆。车子开快了,有些晃,我双手使劲抓牢,生怕被甩下去。当时天黑极了,周围远近都一点儿光亮没有,而只有我身子下面铁条缝隙间,可以看见车轮与铁轨摩擦出的一串串火花。我索性闭上眼睛,心里唯一盼着的就是快点儿停车。没想到的是,火车忽的一下进了一条隧道。隧道里,火车的轰鸣一下子变得无比巨大,好像整个世界都变成声压要把我碾碎。太可怕了,这就是通往地狱的通道。我身子蜷缩着,恐惧地承接着这一切。火车在隧道里足足开了有半个小时,这是我平生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,肯定是我所能承受的极限!
万幸那列火车应该是不是烧煤的,否则煤烟也肯定会把我呛死。火车出了隧道又开了一段时间,我感觉到车减速了,还不断地变岔道,知道要停车了,熬过来了。
由于上车的时候太乱,以致大家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。大家都急的够呛,当我再次见到大家的时候,都乐坏了。特别是我的妹妹。
火车进了编组站,广播里不断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编组口令。谁知道我们这车还走不走啊?我下车找了一位扳道工,扳道工看出我们是知青,就说这车不走了,旁边这车走,上旁边车吧。
扒火车
我们全都下了车,到旁边车上一看,原来是一辆运煤车。上吧,没办法。几个人就在高高的煤堆上坐了下来,车很快就开了,等速度开起来,车倒是不晃,但一阵一阵颠得厉害。我们都坐在高处,连个能扶的地方也没有,只能互相紧拉着手。而我腾出一只手,死劲扒住一个大煤块。当时还是黑夜,七八个人坐在煤车顶上,随时都有被颠下来的危险。这个场景,常人绝难想象。
天蒙蒙亮,车停了。忽然看见从后面煤车上爬起来几个人,满身满脸都是黑的,其中一人还戴着眼镜,形象就像刑场上的政治犯。原来他们也是扒车回北京的知青。看到他们,我们都笑了。再看看自己,其实一毬样。我们都是“政治犯”。
大家一起下了车。那是一个很小的客车站,有个非常小的候车室,候车室门前有个卖早点的摊儿。大家在自来水管那儿洗了洗脸,吃了油饼大米粥,就又进到站里,准备再找辆车往郑州走。建民找到我,说站里有一群人一直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,说咱们得提防着点。我原来没注意,经建民一提醒,我也觉得确实有问题。我说咱们赶快找个车厢躲进去。我们找了个空车厢,为了防身,我们特意从铁轨旁搬上来一堆石块儿。
车开了,车站上那些人从开着的车门看见了我们,他们开始用石块砍我们,我们也开始用石块还击,我们一边还击一边哈哈笑,心想车开了,你们想追也追不上啦。
车开出一、二百米忽然停了,紧接着又往回倒,竟又倒回车站里,只不过是换了旁边的另一条轨道,原来车是在换轨。这把我们可吓坏了,只能关上车门躲着。幸好车又开了,直到真的开起来大家才放下心。一分析,估计我们第一次走的时候,那帮人也没想到车还会回来,就散了。躲过一劫。
 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
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