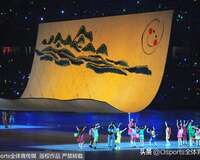一个北京知青的夏县记忆(15)
2024-01-19 来源:你乐谷
”,听不见叫“不贴贴(bùtiētiè)”,牲畜叫“头牯”,蹲下叫“蹴下”,蹲着叫“搁蹴着”,抽烟卷叫“吃纸烟(cīzīyān)”,摔跤叫“挒跤”,头叫“滴喽”,脖子叫“脖项(pòhàng)”,眼睛叫“眼窝(niānwò)”,眼瞎叫“瞎眼窝(hàniānwò)”,鼻子叫“批疙瘩(pīgeda)”,头发叫“头毛”,屁股叫“沟”,馒头叫“馍”,烙饼叫“烙馍(luōmuò)”,油饼叫“油煮馍(yōubūmò)”,面条叫“齐子”,麻花叫“麻堂”,辣椒叫“麻椒”,咸菜叫“汉(hàn)菜”,玉米叫“玉茭”或“玉桃芙”,高粱叫“草桃芙”,黄豆叫“白豆(piètōu)”,绿豆叫“六豆(lìutōu)”,西红柿叫“海柿”,香菜叫“芫荽”,苤蓝叫“车莲”,茄子叫“恰”,桑叫“梭”,地头叫“地脚头(dìjuétòu)”,稀疏叫“沙”,短裤叫“裤衩衩”,小褂叫“汗塌塌”,鞋叫“孩”,火柴叫“呲火”,茅房叫“茅后头”,面缸叫“瓮”,最常见的一种灰色瓮叫三斗瓮,能装三斗粮食,筐叫“撮”(屁股也叫“撮”),中午叫“晌午”,昨天叫“压个”,昨晚叫“压黑(yǎhè)”,夜里叫“黑了间(hēlejiān)”,明天叫“明个”,盖房的土坯叫“糊秸”,做土坯叫“打糊秸”,周公之礼叫“打肉糊秸”,麻烦叫“麻达(màdà)”,小气叫“稀发”,小气鬼叫“稀发鬼”,捣蛋鬼叫“捣事毛”,胡说叫“胡鳖说(hùbiēfiè)”,奇怪叫“老鳖怪”(鳖是脏话的变音),谈及、说过叫“说及(fiējì)”,感兴趣叫“感冒”,吃胖了叫“吃细”了,粘叫“然”,抹墙的黄土里加上的花秸也叫“然”,煤叫“大烟炭”,拉磨牲口的眼罩叫“暗眼(ānyǎn)”,吆喝牛往左往右叫“哒哒、咧咧”,吆喝骡马有意思,前进叫“吁”,停止叫“驾”,这与北京这边恰恰相反,风马牛不相及了?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的数据报告表明,世界上现存6000多种语言当中,有一半左右处于衰败甚至消亡的过程中,有200种语言不超过三代人就会彻底灭绝。我不知道方言算不算语言的一个亚种,夏县方言也快灭绝了吧?我原来房东文来的儿子宝军很多当地话都不会了。
我和逊白都非常喜欢那边的话,有时也会说上一两句。比如每次包饺子,馅儿调好了要开始包,都会说一句“勾加”,颇有仪式感。
69年村里来了几位干部,是县里下放蹲点的。老魏分到了我们七队。老魏人非常好,他想给队里搞些收入,就带领大家建了一间豆腐作坊。做豆腐工序很多,但也不算太难,就是点豆腐要有技术,是要老魏亲自做的。全过程我都看了,豆腐坊里很香,热气腾腾的。那头驴子也在屋里拉磨磨豆浆。
老魏对我很好,是他把我抽调大队去写标语的。要不是他,我真不知道我能写那么大的字。他是城关人,离堡尔村十来里路,但口音跟这里很有些不一样,这就是“五里不同音”吧。去县城路过五里桥,那里有个村子叫桥下街,那里其实是又无桥又无街,老乡有个顺口溜:“五里桥,桥下街,走到桥下木(没)一些。”这用当地话说起来很顺口也很好听,多年没忘。
其实让我忘不了五里桥的是我们曾在那里与当地农民打了一架,我、树臣、宝琛。一日,我三人进城,在路上有人骑车刮了我们一下,树臣揪住那人非让他道歉,那人很不情愿地道了歉,我们就走了。下午我们从城里回来,走到五里桥河滩时有些累,三人便坐在土台上休息。忽然看到一群人,大约十几个小伙子呼喊着跑了过来,手里还举着锄头棍棒之类,一看便是来打架的。我们赶忙站起,那些人不由分说上来便打,双方打作一团。我是左撇子,这在打架时会占些便宜,一拳将一人嘴打出血了。接着我转身爬上一块高地,那里有大量的大块鹅卵石,我举起一块鹅卵石朝一人砸过去,没有砸到,正准备再搬石头,忽然看到宝琛被人用锄头打在额头,血哗地流了下来,白衬衫都染红了。我吓坏了,便大声喊停。其实对方见到流血也吓着了,大家停了下来,我和树臣架着宝琛往县医院跑。宝琛额头上被锄头砍了一个很深的口子,医院里缝了针包扎好才止住血。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的数据报告表明,世界上现存6000多种语言当中,有一半左右处于衰败甚至消亡的过程中,有200种语言不超过三代人就会彻底灭绝。我不知道方言算不算语言的一个亚种,夏县方言也快灭绝了吧?我原来房东文来的儿子宝军很多当地话都不会了。
我和逊白都非常喜欢那边的话,有时也会说上一两句。比如每次包饺子,馅儿调好了要开始包,都会说一句“勾加”,颇有仪式感。
69年村里来了几位干部,是县里下放蹲点的。老魏分到了我们七队。老魏人非常好,他想给队里搞些收入,就带领大家建了一间豆腐作坊。做豆腐工序很多,但也不算太难,就是点豆腐要有技术,是要老魏亲自做的。全过程我都看了,豆腐坊里很香,热气腾腾的。那头驴子也在屋里拉磨磨豆浆。
老魏对我很好,是他把我抽调大队去写标语的。要不是他,我真不知道我能写那么大的字。他是城关人,离堡尔村十来里路,但口音跟这里很有些不一样,这就是“五里不同音”吧。去县城路过五里桥,那里有个村子叫桥下街,那里其实是又无桥又无街,老乡有个顺口溜:“五里桥,桥下街,走到桥下木(没)一些。”这用当地话说起来很顺口也很好听,多年没忘。
其实让我忘不了五里桥的是我们曾在那里与当地农民打了一架,我、树臣、宝琛。一日,我三人进城,在路上有人骑车刮了我们一下,树臣揪住那人非让他道歉,那人很不情愿地道了歉,我们就走了。下午我们从城里回来,走到五里桥河滩时有些累,三人便坐在土台上休息。忽然看到一群人,大约十几个小伙子呼喊着跑了过来,手里还举着锄头棍棒之类,一看便是来打架的。我们赶忙站起,那些人不由分说上来便打,双方打作一团。我是左撇子,这在打架时会占些便宜,一拳将一人嘴打出血了。接着我转身爬上一块高地,那里有大量的大块鹅卵石,我举起一块鹅卵石朝一人砸过去,没有砸到,正准备再搬石头,忽然看到宝琛被人用锄头打在额头,血哗地流了下来,白衬衫都染红了。我吓坏了,便大声喊停。其实对方见到流血也吓着了,大家停了下来,我和树臣架着宝琛往县医院跑。宝琛额头上被锄头砍了一个很深的口子,医院里缝了针包扎好才止住血。
 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
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