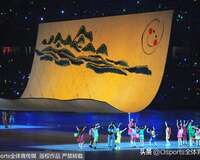一个北京知青的夏县记忆(23)
2024-01-19 来源:你乐谷
那些打人的是天津知青,海河边上练石锁的。听说都进了公安局。我问过其中一个天津女孩,她们与那些人并不认识。
绛县医院住院部有二、三十间病房,每间房住两个病人,陪护的人也在病房里住。医院有食堂,病人和家属都可以在食堂吃饭。但农民一般吃不起食堂,家属都自己做饭。在医院大院子的东墙墙根,有一溜十几个病人自家垒的小灶,每天各家就在自己的小灶给病人做饭。
我和建民在食堂吃饭,饭钱由民工指挥部支付。食堂的饭菜很好,也不是很贵。那个做饭的厨师是个年轻小伙,体格很好的样子,但脸色很差。原来他隔一段时间就在医院里卖一次血,我见过,好像每次能卖20元。别人说,他是食堂做饭的,卖完血能补上。
绛县县城里有一座监狱,大门退缩很深,有持枪岗哨。这就是俗称的县大狱。听绛县人讲,有个你们北京知青是搞写作的,非要到监狱里体验生活,故意犯了点法进去了。
在绛县时到县文化馆去转,见到一个知青模样的人在画油画,一攀谈才知他也是北京知青而且也是高二。他叫杨悠明,是被抽调到县文化馆搞宣传的,每天画画。我在医院看护时间比较富余,于是几乎每天都到他那里。他是大画家董希文的外甥,画画算家学了。文化馆馆长非常好,听说我也画点画,对我非常欢迎,还送给我十支碳铅笔和几份画报。
杨悠明现在是有一定名气的画家了,是带研究生的大学教授。我从绛县回来就与他断了联系。1985年左右,我在北京美协开办的艺术家画廊兼职,正好碰到他送作品参展,遂又见面。也算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吧。
有一次我和宝琛、树臣,好像还有令典去平陆茅津渡送人,回来时没车了,便在长途车站睡了一宿。候车室里有长椅,但臭虫咬得根本不能睡。我是把一捆竹帘子卷在身上在地上胡乱睡了一觉,别人怎么睡的我忘了。天亮以后,车站门前有卖早点的,烧饼夹肉,我们一人买了一个。我饿了,上来几口就吃了一半儿,不知是谁发现肉里有蛆,很小但很多。当时就去找卖烧饼的人理论,全退了,就连我吃了一半的也退了。虽然心里非常恶心,但那香味还是让我不舍。
我仔细看了看,肉是好的,是后来浇上的酱油里面有蛆。记得我去庙前供销社,那里卖酱油的是用纱网篦子把蛆条篦出再卖的。酱油里有蛆应属正常现象。还有,当地人做醋,柿子醋,不好吃,颜色就像淘米水。我们到老乡家要,打开醋缸一看,表面一层白醭,缸边上全是灰白色的小飞虫。
那里人爱说一些顺口溜。比如刚到村里,小娃见了我们会一起说:“大学生,遗额一位纪念章。”二队有个女娃是个憨憨,两筒鼻涕,叫香钏,她只是囫囵着说“大学生,遗额纪念章”。老乡还说我们是“皮底鞋(hài),嘎滴嘎。”所谓皮底鞋不过塑料底鞋而已。
村里还有个顺口溜:“四大家、八小家,二十四家匀和家。”这是说村里早先的生态。村里的姓氏主要是四大姓,杨、赵、姜,还有一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还有些杂姓,比如武、张、闫、卫、郑、孔等,其中杨姓最大,唯一的一家地主好像就是杨姓。
还有些外来户河南人,村里人叫他们河南旦。也有些四川女人,是逃荒嫁过来的。我记得六队有一位,跟任何人都不说话。传说当年50斤全国粮票就能换回一个四川大姑娘。
四队牲口棚很大很干净,它一侧是骡马一侧是牛,加起来有十几头吧。骡子马很少卧下,好像总是站着。而牛则喜欢卧,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倒嚼。它们的饲养员喜欢写字,他在牲口棚门框上写了幅对联:路往忠字上走;血往忠字上流。
牲口棚里很暗,从门口往里看,马的眼睛发绿光,牛的眼睛发红光,宝石似的很好看。小时候家里养过两只猫,大老黄发红光,大老黑发绿光。
队里大宗的口粮是红薯,每年每人都会分三、四百斤。红薯是要放在窖里的,窖就是像井一样垂直挖到地底下大约两丈深处,然后再横着挖几个穴。天宝他爹让给我一个穴,我就学着把红薯一筐一筐系到底下,再小心地一块一块把红薯码整齐。最关键的是红薯不能有外伤,否则会烂,而且会把全窖红薯都传染上。红薯好吃,除了煮着吃,还可以做红薯米汤,还可以到县城附近村粉坊里换粉条吃。中国这个地方实在神奇。红薯、玉米都是外来物种,一经引进都成了最大宗。好像棉花也是。
绛县医院住院部有二、三十间病房,每间房住两个病人,陪护的人也在病房里住。医院有食堂,病人和家属都可以在食堂吃饭。但农民一般吃不起食堂,家属都自己做饭。在医院大院子的东墙墙根,有一溜十几个病人自家垒的小灶,每天各家就在自己的小灶给病人做饭。
我和建民在食堂吃饭,饭钱由民工指挥部支付。食堂的饭菜很好,也不是很贵。那个做饭的厨师是个年轻小伙,体格很好的样子,但脸色很差。原来他隔一段时间就在医院里卖一次血,我见过,好像每次能卖20元。别人说,他是食堂做饭的,卖完血能补上。
绛县县城里有一座监狱,大门退缩很深,有持枪岗哨。这就是俗称的县大狱。听绛县人讲,有个你们北京知青是搞写作的,非要到监狱里体验生活,故意犯了点法进去了。
在绛县时到县文化馆去转,见到一个知青模样的人在画油画,一攀谈才知他也是北京知青而且也是高二。他叫杨悠明,是被抽调到县文化馆搞宣传的,每天画画。我在医院看护时间比较富余,于是几乎每天都到他那里。他是大画家董希文的外甥,画画算家学了。文化馆馆长非常好,听说我也画点画,对我非常欢迎,还送给我十支碳铅笔和几份画报。
杨悠明现在是有一定名气的画家了,是带研究生的大学教授。我从绛县回来就与他断了联系。1985年左右,我在北京美协开办的艺术家画廊兼职,正好碰到他送作品参展,遂又见面。也算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吧。
有一次我和宝琛、树臣,好像还有令典去平陆茅津渡送人,回来时没车了,便在长途车站睡了一宿。候车室里有长椅,但臭虫咬得根本不能睡。我是把一捆竹帘子卷在身上在地上胡乱睡了一觉,别人怎么睡的我忘了。天亮以后,车站门前有卖早点的,烧饼夹肉,我们一人买了一个。我饿了,上来几口就吃了一半儿,不知是谁发现肉里有蛆,很小但很多。当时就去找卖烧饼的人理论,全退了,就连我吃了一半的也退了。虽然心里非常恶心,但那香味还是让我不舍。
我仔细看了看,肉是好的,是后来浇上的酱油里面有蛆。记得我去庙前供销社,那里卖酱油的是用纱网篦子把蛆条篦出再卖的。酱油里有蛆应属正常现象。还有,当地人做醋,柿子醋,不好吃,颜色就像淘米水。我们到老乡家要,打开醋缸一看,表面一层白醭,缸边上全是灰白色的小飞虫。
那里人爱说一些顺口溜。比如刚到村里,小娃见了我们会一起说:“大学生,遗额一位纪念章。”二队有个女娃是个憨憨,两筒鼻涕,叫香钏,她只是囫囵着说“大学生,遗额纪念章”。老乡还说我们是“皮底鞋(hài),嘎滴嘎。”所谓皮底鞋不过塑料底鞋而已。
村里还有个顺口溜:“四大家、八小家,二十四家匀和家。”这是说村里早先的生态。村里的姓氏主要是四大姓,杨、赵、姜,还有一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还有些杂姓,比如武、张、闫、卫、郑、孔等,其中杨姓最大,唯一的一家地主好像就是杨姓。
还有些外来户河南人,村里人叫他们河南旦。也有些四川女人,是逃荒嫁过来的。我记得六队有一位,跟任何人都不说话。传说当年50斤全国粮票就能换回一个四川大姑娘。
四队牲口棚很大很干净,它一侧是骡马一侧是牛,加起来有十几头吧。骡子马很少卧下,好像总是站着。而牛则喜欢卧,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倒嚼。它们的饲养员喜欢写字,他在牲口棚门框上写了幅对联:路往忠字上走;血往忠字上流。
牲口棚里很暗,从门口往里看,马的眼睛发绿光,牛的眼睛发红光,宝石似的很好看。小时候家里养过两只猫,大老黄发红光,大老黑发绿光。
队里大宗的口粮是红薯,每年每人都会分三、四百斤。红薯是要放在窖里的,窖就是像井一样垂直挖到地底下大约两丈深处,然后再横着挖几个穴。天宝他爹让给我一个穴,我就学着把红薯一筐一筐系到底下,再小心地一块一块把红薯码整齐。最关键的是红薯不能有外伤,否则会烂,而且会把全窖红薯都传染上。红薯好吃,除了煮着吃,还可以做红薯米汤,还可以到县城附近村粉坊里换粉条吃。中国这个地方实在神奇。红薯、玉米都是外来物种,一经引进都成了最大宗。好像棉花也是。
 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
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