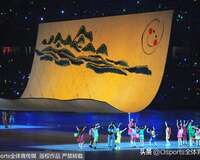一个北京知青的夏县记忆(8)
2024-01-19 来源:你乐谷
文革中,某人言:我不是红五类但我红五类观点!
夏县插队的某某平日寡语。在校时,一日班里开会,此人慷慨疾言,其略云:都说老子有自来红思想,说老子进了什么红色保险箱,老子红了怎么了?老子今天还他妈就红了,红到底了!
掌声雷动。
文革中的辩论会,谁若发言,会有人高喊“报出身!报出身!”,如果回答是红五类,同样掌声雷动。
村里某同学某日在大队部翻看书记笔记本,看到了全村知青的出身。一言以蔽之,没什么好的。
5.队中骡牛
我们七队有三头大牲畜,其中一匹骟骡,身材高大,毛色棕黑油亮,性情温顺,大家叫它“老骟”,它驾辕。还有一匹母骡,毛色棕黄,蹄子有毛病,后两蹄的铁掌都往前探出一段略弯的铁条,这样才好走路。它叫“踢踢”,脾气不好,是拉边套的。还有一匹小个子花青马,也是拉边套的。有一年夏收,它们一趟趟从地里往场院拉麦捆。后来可能实在太累了,路过牲口圈大门前,它们忽然猛地斜着拐了进去,大车把放在墙边的一排防火用的盛水大缸全撞碎了。赶车人没有责打它们,社员们也都不怪它们。
“踢踢”后来真的闯了大祸,它把饲养员天才踢死了。
我们队有一头母驴,它生了一头小驴。队上想让它再生匹骡子,于是就派我牵着它到公社配种站配种。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后代,公驴母马生出的是我们通常见到的骡子,而公马母驴生出来的则为驴骡。驴骡体型较小相貌丑陋,但也算是大牲畜了。我到了配种站,人家说过了晌午来取吧,我就去了两里之外的薛庄宝琛那里。过了晌午我把驴领回来,过了桥之后我就骑了上去。开始还好,走了一半路,驴突然狂奔起来,我想下都下不来了。过一个小坡时我趁机跳下,结果一把没抓住,驴自己跑了。我怕它跑丢了,就玩儿命追,但根本追不上,一会儿就看不见了。等我跑回牲口圈,它正在那里给自己的小驴喂奶呢。
后来才知道,七队的妇女们正在那边地里干活,她们看见我在追驴,都乐弯了腰。
配种站里有个大院子,墙边的柱子上拴着两匹种马,一头种驴。我牵着我们队的母驴一进院门,所有的种马种驴全都躁动起来,嘶叫不已,前蹄使劲刨地,眼白都露出来了。《动物画技法》中说,马只有过度兴奋或过度惊恐时才会露眼白。那两匹种马非常漂亮,毛色油光泛着蓝色。种驴亦十分壮硕。据说它们每天还要吃鸡蛋呢。
1972年我和逊白在庙前邮电所门前看见一头拴在那里的小驴,乖乖的一动不动,摸它、揪它耳朵也没事。它的眼睛非常好看,深灰色,温润朦胧,长睫毛,大大的。它脖套圈上用毛笔写着“小灰驴”三个字,看来它就叫小灰驴了。我们俩陪小灰驴呆了好长时间。
我也放过牛。七队有十几头黄牛,大小都有。它们平常干活不多,就是耕地时用它们。放牛就是让他们到柳沟埝那边的河滩上吃草。从村里到柳沟埝要走一段路,路两旁都是玉米地,有几头牛非要到地里走,把玉米杆都踩倒了,打也没用,刚一转脸又进去了,可能是想吃嫩玉米吧。有个老农说它欺负你嘞,看你是新人。牛是蔫儿坏的家伙。
我也用牛犁过地,两头黄牛。让它们往左往右是吆喝“哒哒”、“咧咧”,但它们不怎么听我的,还是欺负新人。
6.生活实录
刚下乡头一年,我们的口粮是有关部门下发的,每人每月44斤原粮,就是没有磨成粉的麦粒、玉米粒。我是个口无遮拦之人,当时我就说,44斤肯定是精确计算出来的一个数,你该吃多少早有人给你算清楚了,同时给你留下一道数学题,44斤原粮等于多少斤磨好的面?
麦粒和玉米粒磨成粉,这一定要有机械或器械去做。幸亏村里有电磨坊,自己先要把麦粒或玉米粒淘洗、晾晒干,然后推到三队那边的磨坊去磨成面。由于时不时会停电,所以经常要排很长时间的队。而一切操作都是自己去做的,粮食颗粒要放到上面的漏斗里,磨出来的碎颗粒会在筛子上筛,筛出来的就是面,没筛过的要重新放回漏斗再磨。比如麦子,先筛出来的叫头茬面,非常白非常好,再筛出来的就要差些,再往后就更差。从筛出来面的颜色就可以看出,明显是越来越黑。一般的是把头茬面先收起来单放,二、三茬再另放,也不能磨得太狠,总要剩下15%左右的麦麸的,我想北京的85粉应该就是这么来的。当然也有人是一箩到底的,那叫通麦,虽然出粉率高,但很不好吃,甚至不如玉米面。头茬面特别好,蒸出馍来雪白雪白,当地人叫“雪白馍”(读作xuēpiēmo)。
夏县插队的某某平日寡语。在校时,一日班里开会,此人慷慨疾言,其略云:都说老子有自来红思想,说老子进了什么红色保险箱,老子红了怎么了?老子今天还他妈就红了,红到底了!
掌声雷动。
文革中的辩论会,谁若发言,会有人高喊“报出身!报出身!”,如果回答是红五类,同样掌声雷动。
村里某同学某日在大队部翻看书记笔记本,看到了全村知青的出身。一言以蔽之,没什么好的。
5.队中骡牛
我们七队有三头大牲畜,其中一匹骟骡,身材高大,毛色棕黑油亮,性情温顺,大家叫它“老骟”,它驾辕。还有一匹母骡,毛色棕黄,蹄子有毛病,后两蹄的铁掌都往前探出一段略弯的铁条,这样才好走路。它叫“踢踢”,脾气不好,是拉边套的。还有一匹小个子花青马,也是拉边套的。有一年夏收,它们一趟趟从地里往场院拉麦捆。后来可能实在太累了,路过牲口圈大门前,它们忽然猛地斜着拐了进去,大车把放在墙边的一排防火用的盛水大缸全撞碎了。赶车人没有责打它们,社员们也都不怪它们。
“踢踢”后来真的闯了大祸,它把饲养员天才踢死了。
我们队有一头母驴,它生了一头小驴。队上想让它再生匹骡子,于是就派我牵着它到公社配种站配种。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后代,公驴母马生出的是我们通常见到的骡子,而公马母驴生出来的则为驴骡。驴骡体型较小相貌丑陋,但也算是大牲畜了。我到了配种站,人家说过了晌午来取吧,我就去了两里之外的薛庄宝琛那里。过了晌午我把驴领回来,过了桥之后我就骑了上去。开始还好,走了一半路,驴突然狂奔起来,我想下都下不来了。过一个小坡时我趁机跳下,结果一把没抓住,驴自己跑了。我怕它跑丢了,就玩儿命追,但根本追不上,一会儿就看不见了。等我跑回牲口圈,它正在那里给自己的小驴喂奶呢。
后来才知道,七队的妇女们正在那边地里干活,她们看见我在追驴,都乐弯了腰。
配种站里有个大院子,墙边的柱子上拴着两匹种马,一头种驴。我牵着我们队的母驴一进院门,所有的种马种驴全都躁动起来,嘶叫不已,前蹄使劲刨地,眼白都露出来了。《动物画技法》中说,马只有过度兴奋或过度惊恐时才会露眼白。那两匹种马非常漂亮,毛色油光泛着蓝色。种驴亦十分壮硕。据说它们每天还要吃鸡蛋呢。
1972年我和逊白在庙前邮电所门前看见一头拴在那里的小驴,乖乖的一动不动,摸它、揪它耳朵也没事。它的眼睛非常好看,深灰色,温润朦胧,长睫毛,大大的。它脖套圈上用毛笔写着“小灰驴”三个字,看来它就叫小灰驴了。我们俩陪小灰驴呆了好长时间。
我也放过牛。七队有十几头黄牛,大小都有。它们平常干活不多,就是耕地时用它们。放牛就是让他们到柳沟埝那边的河滩上吃草。从村里到柳沟埝要走一段路,路两旁都是玉米地,有几头牛非要到地里走,把玉米杆都踩倒了,打也没用,刚一转脸又进去了,可能是想吃嫩玉米吧。有个老农说它欺负你嘞,看你是新人。牛是蔫儿坏的家伙。
我也用牛犁过地,两头黄牛。让它们往左往右是吆喝“哒哒”、“咧咧”,但它们不怎么听我的,还是欺负新人。
6.生活实录
刚下乡头一年,我们的口粮是有关部门下发的,每人每月44斤原粮,就是没有磨成粉的麦粒、玉米粒。我是个口无遮拦之人,当时我就说,44斤肯定是精确计算出来的一个数,你该吃多少早有人给你算清楚了,同时给你留下一道数学题,44斤原粮等于多少斤磨好的面?
麦粒和玉米粒磨成粉,这一定要有机械或器械去做。幸亏村里有电磨坊,自己先要把麦粒或玉米粒淘洗、晾晒干,然后推到三队那边的磨坊去磨成面。由于时不时会停电,所以经常要排很长时间的队。而一切操作都是自己去做的,粮食颗粒要放到上面的漏斗里,磨出来的碎颗粒会在筛子上筛,筛出来的就是面,没筛过的要重新放回漏斗再磨。比如麦子,先筛出来的叫头茬面,非常白非常好,再筛出来的就要差些,再往后就更差。从筛出来面的颜色就可以看出,明显是越来越黑。一般的是把头茬面先收起来单放,二、三茬再另放,也不能磨得太狠,总要剩下15%左右的麦麸的,我想北京的85粉应该就是这么来的。当然也有人是一箩到底的,那叫通麦,虽然出粉率高,但很不好吃,甚至不如玉米面。头茬面特别好,蒸出馍来雪白雪白,当地人叫“雪白馍”(读作xuēpiēmo)。
 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
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