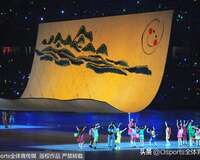一个北京知青的夏县记忆(4)
2024-01-19 来源:你乐谷
刚到村里时,几乎每晚都会有老乡到我们住的屋里坐,语言不通,只是握着手对你笑。后来渐渐没人来了。原来老乡开始以为这些知青是工作组,来蹲点儿整人的,有些不尴不尬的人怕被整就先行疏通,后来听说我们什么也不是,就“算毬”了。
我所在的七队,队长叫老八,人憨厚,不识字。一次公社开会回来给社员传达两项内容,一是中央发生了“二月逆流”,二是要搞“合作医疗”。老八说了半天也没说清,最后问大家:哪位参加“二月逆流”,报名。众愕然。用当地方言去讲“二月逆流”与“合作医疗”,确实有些纠缠不清。还有一次讲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,当地人理解为“破裂又捏住”,语音极其相似。
我们那边农村,家家都装了一个有线喇叭,每早六点播放新闻。老乡们拿开播曲《东方红》当闹钟用。树臣与我邻村,他讲那次召开“九大”的新闻是夜里十二点播的,一老农听到《东方红》就下地干活。过了半天儿,老农有些纳闷,都往菜地里挑了六担粪了,天怎么还没亮?
插队第二年的春天,老六的老伴死了,这是一件白事。七队的男人差不多都去了,也叫上我,表示对我的接纳吧。大家一起在老六家院子里吃了席,无外乎是两样面馍,红薯米汤,豆腐、青菜、粉条、辣子之类。吃完饭青壮年一起抬棺,往东面山坡上走,路上换了几次人手。坡上已经有人挖好了坑,目测三米长两米宽四米深,东西走向,底部靠东横着还有个东西走向的暗穴。大家用绳子将棺材吊到坑底但并不完全放下,而是东边暗穴里有个人一点点将棺材纵向移进穴里,安放好了,那人再从棺材上边的缝隙爬出来。等人上来了,大家就开始往坑里填土。填到一半时候,老孔冷不丁说了句:“人吃一辈子土,到底让土吃一口。”听到这话,大家似乎一愣,许久没人说话,只有一锹一锹的铲土声。老孔是河南逃难过来的,一个人住在村边的一间小房里。整天乐呵呵,嘴里哼着豫剧小调。他叫孔祥超,是祥字辈的,说跟孔祥熙平辈。
刚到那边可能是水土不服,有一天夜里我鼻子大出血,可怕的是我睡着了自己根本不知道。是一次翻身时觉得枕头黏糊糊的,手电一照,枕头、被头以及脸上全是粘稠的血。赶紧起来用凉水洗脸,好歹把血止住了。但血流的实在太多了,第二天枕头被子洗出好几盆血水来。想起后怕,幸亏我自己醒了,否则失血过多是要出人命的。医疗手册上就是这么说的。
1969年,县城修了一个游泳池。知青乐坏了,十几、二十几里路跑去游泳。票价5分。游泳的全是知青。买票的人中也有当地农民,他们不游泳,只是戴个草帽,一声不吭蹲在池边。当地有传言:5分钱看女学生大腿。
夏县女子讲究不露肉,手臂、脚踝都不外露。他们看到女知青穿裙子稀罕,戏称其为“沟打伞”。当地人管屁股叫“沟”,故称。
一次去庙前赶集,我、树臣、宝琛三人在集上逛。树臣看到一位老农胡乱戴着个口罩,口罩脏的全成黑的了。树臣乐得不行,说,他戴口罩干嘛,嫌空气干净么?
夏县是全国绿化县,树的确非常多。柳沟埝边是柳树,道边是杨树,山头散乱的是柿子树,果园里还有不少杏树和梨树。杨树有三种,大叶杨、小叶杨和加拿大杨。老乡都说,加拿大杨是白求恩送的。杨树成不了什么材,但它长得非常快,树枝树叶还是非常好的柴火。那里都烧柴锅,柴火需求量很大,主要是玉米秸、麦秸,再有就是杨树枝了。杨树枝并不需要晾干,从树上砍下来直接烧就可以,烧时它叶子里还会冒出些油来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。老乡家里都有一根长杆,顶上有一把向上的弯刀,使劲一怼树枝就下来了,这个他们叫铦(kuō)。道边杨树树冠都很高,就是因为下面的枝条都被铦掉了。
1969年春天是夏县掌权一派的庆典,他们要各村各大队都要扎花车搞游行汇演。村里着实忙活起来,挑了一辆最好的大车,上面搭上车棚,全车满用花布缠绕,四角扎彩球,车棚中坐着几位浓妆艳抹的小媳妇。拉车的骡子一共五匹,毛色油光闪亮,我们队的老骟驾辕,车把式响鞭开道,煞是威风。全县各大队都下足了功夫,争奇斗艳各显其能。什么庆典,就是民间社戏。春节样板戏也如是,百姓总要、也总会找到自己的欢娱,管你谁革命、谁掌权。
我所在的七队,队长叫老八,人憨厚,不识字。一次公社开会回来给社员传达两项内容,一是中央发生了“二月逆流”,二是要搞“合作医疗”。老八说了半天也没说清,最后问大家:哪位参加“二月逆流”,报名。众愕然。用当地方言去讲“二月逆流”与“合作医疗”,确实有些纠缠不清。还有一次讲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,当地人理解为“破裂又捏住”,语音极其相似。
我们那边农村,家家都装了一个有线喇叭,每早六点播放新闻。老乡们拿开播曲《东方红》当闹钟用。树臣与我邻村,他讲那次召开“九大”的新闻是夜里十二点播的,一老农听到《东方红》就下地干活。过了半天儿,老农有些纳闷,都往菜地里挑了六担粪了,天怎么还没亮?
插队第二年的春天,老六的老伴死了,这是一件白事。七队的男人差不多都去了,也叫上我,表示对我的接纳吧。大家一起在老六家院子里吃了席,无外乎是两样面馍,红薯米汤,豆腐、青菜、粉条、辣子之类。吃完饭青壮年一起抬棺,往东面山坡上走,路上换了几次人手。坡上已经有人挖好了坑,目测三米长两米宽四米深,东西走向,底部靠东横着还有个东西走向的暗穴。大家用绳子将棺材吊到坑底但并不完全放下,而是东边暗穴里有个人一点点将棺材纵向移进穴里,安放好了,那人再从棺材上边的缝隙爬出来。等人上来了,大家就开始往坑里填土。填到一半时候,老孔冷不丁说了句:“人吃一辈子土,到底让土吃一口。”听到这话,大家似乎一愣,许久没人说话,只有一锹一锹的铲土声。老孔是河南逃难过来的,一个人住在村边的一间小房里。整天乐呵呵,嘴里哼着豫剧小调。他叫孔祥超,是祥字辈的,说跟孔祥熙平辈。
刚到那边可能是水土不服,有一天夜里我鼻子大出血,可怕的是我睡着了自己根本不知道。是一次翻身时觉得枕头黏糊糊的,手电一照,枕头、被头以及脸上全是粘稠的血。赶紧起来用凉水洗脸,好歹把血止住了。但血流的实在太多了,第二天枕头被子洗出好几盆血水来。想起后怕,幸亏我自己醒了,否则失血过多是要出人命的。医疗手册上就是这么说的。
1969年,县城修了一个游泳池。知青乐坏了,十几、二十几里路跑去游泳。票价5分。游泳的全是知青。买票的人中也有当地农民,他们不游泳,只是戴个草帽,一声不吭蹲在池边。当地有传言:5分钱看女学生大腿。
夏县女子讲究不露肉,手臂、脚踝都不外露。他们看到女知青穿裙子稀罕,戏称其为“沟打伞”。当地人管屁股叫“沟”,故称。
一次去庙前赶集,我、树臣、宝琛三人在集上逛。树臣看到一位老农胡乱戴着个口罩,口罩脏的全成黑的了。树臣乐得不行,说,他戴口罩干嘛,嫌空气干净么?
夏县是全国绿化县,树的确非常多。柳沟埝边是柳树,道边是杨树,山头散乱的是柿子树,果园里还有不少杏树和梨树。杨树有三种,大叶杨、小叶杨和加拿大杨。老乡都说,加拿大杨是白求恩送的。杨树成不了什么材,但它长得非常快,树枝树叶还是非常好的柴火。那里都烧柴锅,柴火需求量很大,主要是玉米秸、麦秸,再有就是杨树枝了。杨树枝并不需要晾干,从树上砍下来直接烧就可以,烧时它叶子里还会冒出些油来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。老乡家里都有一根长杆,顶上有一把向上的弯刀,使劲一怼树枝就下来了,这个他们叫铦(kuō)。道边杨树树冠都很高,就是因为下面的枝条都被铦掉了。
1969年春天是夏县掌权一派的庆典,他们要各村各大队都要扎花车搞游行汇演。村里着实忙活起来,挑了一辆最好的大车,上面搭上车棚,全车满用花布缠绕,四角扎彩球,车棚中坐着几位浓妆艳抹的小媳妇。拉车的骡子一共五匹,毛色油光闪亮,我们队的老骟驾辕,车把式响鞭开道,煞是威风。全县各大队都下足了功夫,争奇斗艳各显其能。什么庆典,就是民间社戏。春节样板戏也如是,百姓总要、也总会找到自己的欢娱,管你谁革命、谁掌权。
 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
东京热最残暴的一部的番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