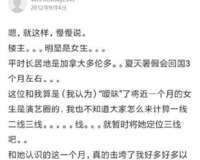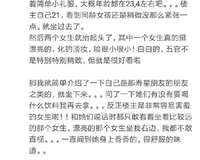用散文写成的一个电影故事
2024-01-19 来源:你乐谷

我喜欢电影的散文化,它有一种独特的叙说和抒情方式,也非常自我。
起初大约只是个别编导的一种文化偏好,后来逐渐成为作品的一种类型风格。
不再追求戏剧和电影里扣人心弦的情节紧张,以牺牲或淡化故事性的跌宕起伏为代价,更偏重意识流方式,舒缓的安静的展开记事。
正因为没有了情节的张力做支撑、来吸睛,对电影编导和主角的表演水准要求更高。
琐碎的片段化叙事,消退了编导对剧情掌控的欲望,你看到的就是你的现实。
真实性、真诚度和情绪的收敛尺寸皆为试金石。
蒋雯丽出手就不凡。
《我们天上见》这部影片的文学性出乎意料的浓郁,它的可读性超出了一部影片的价值。
好像带我们一起去拾起落在时光里的残叶,上面写着什么当初你并不知道。
现在似乎明白了一些,但还是有些困惑。
一首那个时代耳熟能详的歌曲“远飞的大雁”,用当时流行的口琴简单而缓缓奏出的时候,那个余味深长的结尾,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一种触碰心灵的内在力量,禁不住让人潸然泪下。
影片的选材并不算新颖。
它讲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发生在蚌埠的一些事情:双亲不在身边的女孩小兰,与姥爷之间相互扶持,情感真挚的一段人生经历。
这种题材虽然自带感染力,也很容易给人以触动,但要打破同类型选材的窠臼,重塑出新的亮点来则很难。
影片形成的几个点是特别值得咀嚼的。
其一是祖孙相互扶持命运的反转。
小兰三岁那年,父母因为政治原因,被送到新疆的劳改农场,一去就是十年。从那开始,小姑娘被年长她八十岁的姥爷照顾。
小兰在姥爷的戒尺和关爱下翻着跟头长大了。
戒尺好像就是个隐喻。
破四旧立四新也好,文革砸烂多少人的狗头也罢,老辈人心中的戒尺始终屹立着,从未被动摇过。
影片里戒尺这个道具用得真好。
童年的小兰被戒尺惩戒出对错、是非感,从不理解的嗷嗷大哭,到主动拿戒尺申领处罚,一天天在长大。
某一天起,姥爷已经衰老到再难照顾外孙女,甚至很难再吞咽食物时,小兰拿起了戒尺,“逼”着姥爷吃一口。
那种细腻的温情,在一把小小的戒尺上满满的溢出。
戒尺也是一种宣示:中国人的伦理传统无论遭受过多少践踏,它都斑斑驳驳的保存了下来,依然是中国人族性里的一种本质。
眼睛能够晃动的布娃娃也成为细节上的亮点。
它是遭受委屈的小兰的玩伴、朋友、亲人,一种令人窒息的没有回音的孤寂感由布娃娃衬托出。
到再无力气陪外孙女走在生命的旅途,布娃娃抱在姥爷怀里,又成为无力无奈的姥爷的玩伴、朋友、亲人。
生命的无助,即便有爱也是悲伤。
小兰初练体操劈叉痛得大哭,八十多岁的姥爷在耍猴逗乐她。
姥爷已经衰老得不认人,长大的小兰坐在杠子上去逗姥爷。
这种生命相互搀扶的叙述,每一处心碰触到都是泪点。
姥爷对好人的定义就两条:不扯谎,多帮人做好事。
但一生活得端端庄庄的他,却扯了个时间最长、动作幅度最大的谎言。
姥爷一直模仿爸妈的语气往家里来信,为了安抚小兰,让孩娃别再去找爸妈,他又模仿他们的语气写信来要孩子听话,并时不时的以孩子父母的名义奖励孩子两个哈密瓜。
善良的谎言是对人性的讴歌,恰恰成为影片的动人的光彩。
影片最见功力之处,它对时代痛点的叙述是不动声色的。
 AV丝袜福利一区区电影
AV丝袜福利一区区电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