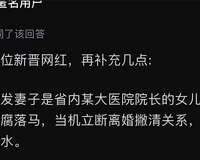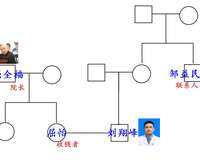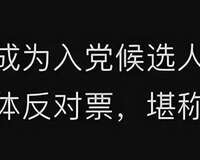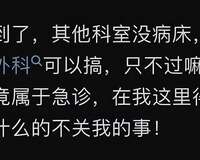小院(二)
2024-01-19 来源:你乐谷
冬日的早晨,寒风把窑洞里窗棱上的棉纸吹得胀弛不定,发出低沉逼人的声响。黑暗中,姥姥用手在枕边摩挲着,划亮一根火柴,满屋填满昏黄的光。接着,点亮从炕头的小桌旁取出满是油腻的灯盏,煤油灯立即升起黄豆大小跳动的火苗。炕的一头,姥爷宽厚的胸膛里,发出均匀宏厚的鼾声,偶尔还说着含糊不清的梦话。
“快起,快起,不然会误了学堂”,姥姥催促着。姥爷不经意地翻转身,鼾声停歇片刻,又开始了。我坐起身,眼皮不争气地被眼屎糊着,本就不大的眼睛,费了半天劲才睁开一只,我接过姥姥递过来的棉袄,烦躁地扣着衣服的扣子。扣错了,又发着莫明的火气。我真想如姥爷一样赶紧变老,做着自己香甜的梦,再不用起早贪黑地上早读了。
瓦窑头小学在村子中间。整个冬季,每天早晨教室里都要重新生火。从废旧的作业本撕下几页纸,塞进炉膛里引燃学生自带的“玉米棒棒”。潮湿时,满教室的烟呛得同学们不住地咳嗽,流泪。窗户又没有一块玻璃,只有学生东拼西凑地找来的油布,用图钉钉死在窗扇上。
轮到值日打扫卫生,还要带上自家的笤帚。人年少时都爱表现,而姥姥又不同意让我带走那把家里最好的笤帚。我先是软磨硬缠,无果后满地打滚,最后变得怒目而视。直到姥爷悄悄地转移给我,我又立即破涕为笑。任抹在两袖上的鼻涕、眼泪、口水,被迎面而来的冷风,打造成瓦窑头最晶莹的琥珀。我扫地时等不及酒水,便夸张地挥舞着家什,教室外顿时尘土飞扬,同学们像过雷区一样跑步穿越。我想获得班主任赞许的小小愿望,终究变成失望。那把周正的高梁糜枝笤帚,被折断了几根穗子,我心生愧意。
又到了晚上,土炕上我把被子折叠,一半睡在身子下面,一半盖在身子上面,衣服又盖在腿部,增强后半夜御寒的能力。“人暖腿,狗暖嘴”,姥姥说着,接着打了个呵欠,把右手伸到背后,搔了掻她的左肩。姥爷才听着杂音不小的广播,嘴里还没哼几句蒲剧的曲调,之后不久便发出沉稳的鼾声,似乎从来不关心天塌下来,将会怎么办的问题。为了温饱问题,老鼠也会出来巡游,常常在锅台边碗柜间与姥姥对峙。
多年以后,我用在瓦窑头读书学会的词句给姥爷写信,托二舅带回去,姥姥不识字,但她听到姥爷一字一句地念着,仍然情不自禁地在灶台边撩起围裙,拭去填补挂念的泪珠儿。同样,姥爷语重心长的回信,润湿了我长久的记忆。
人到中年,怀旧的思绪渐渐浓烈。我把一粒粒关于瓦窑头的文字,蘸满情思,种在心间,等春天到来,吐出一簇簇思念的芽尖。

“快起,快起,不然会误了学堂”,姥姥催促着。姥爷不经意地翻转身,鼾声停歇片刻,又开始了。我坐起身,眼皮不争气地被眼屎糊着,本就不大的眼睛,费了半天劲才睁开一只,我接过姥姥递过来的棉袄,烦躁地扣着衣服的扣子。扣错了,又发着莫明的火气。我真想如姥爷一样赶紧变老,做着自己香甜的梦,再不用起早贪黑地上早读了。
瓦窑头小学在村子中间。整个冬季,每天早晨教室里都要重新生火。从废旧的作业本撕下几页纸,塞进炉膛里引燃学生自带的“玉米棒棒”。潮湿时,满教室的烟呛得同学们不住地咳嗽,流泪。窗户又没有一块玻璃,只有学生东拼西凑地找来的油布,用图钉钉死在窗扇上。
轮到值日打扫卫生,还要带上自家的笤帚。人年少时都爱表现,而姥姥又不同意让我带走那把家里最好的笤帚。我先是软磨硬缠,无果后满地打滚,最后变得怒目而视。直到姥爷悄悄地转移给我,我又立即破涕为笑。任抹在两袖上的鼻涕、眼泪、口水,被迎面而来的冷风,打造成瓦窑头最晶莹的琥珀。我扫地时等不及酒水,便夸张地挥舞着家什,教室外顿时尘土飞扬,同学们像过雷区一样跑步穿越。我想获得班主任赞许的小小愿望,终究变成失望。那把周正的高梁糜枝笤帚,被折断了几根穗子,我心生愧意。
又到了晚上,土炕上我把被子折叠,一半睡在身子下面,一半盖在身子上面,衣服又盖在腿部,增强后半夜御寒的能力。“人暖腿,狗暖嘴”,姥姥说着,接着打了个呵欠,把右手伸到背后,搔了掻她的左肩。姥爷才听着杂音不小的广播,嘴里还没哼几句蒲剧的曲调,之后不久便发出沉稳的鼾声,似乎从来不关心天塌下来,将会怎么办的问题。为了温饱问题,老鼠也会出来巡游,常常在锅台边碗柜间与姥姥对峙。
多年以后,我用在瓦窑头读书学会的词句给姥爷写信,托二舅带回去,姥姥不识字,但她听到姥爷一字一句地念着,仍然情不自禁地在灶台边撩起围裙,拭去填补挂念的泪珠儿。同样,姥爷语重心长的回信,润湿了我长久的记忆。
人到中年,怀旧的思绪渐渐浓烈。我把一粒粒关于瓦窑头的文字,蘸满情思,种在心间,等春天到来,吐出一簇簇思念的芽尖。
 年龄最小小的番号
年龄最小小的番号